老广记忆|东涌的丝瓜
如今的城市寸土寸金,
鲜有自家种丝瓜的经历。

去年深秋,我到梅州某生态园旅游,见到了一条条老丝瓜,于是,很想找一条带回家,可惜此处的老丝瓜已经瘦瘦弱弱,与记忆中的老丝瓜相差甚远,顿时没了摘下的念头。但又觉得若不带上一两条回去,隐隐间很是不甘。纠结之际,听朋友说,广州东涌的绿道上便有丝瓜,何必舍近求远。 回来后打听了一下,东涌隶属广州番禺,离广州市区确实很近,于是在某个周末,约上了三五知己去游赏。 相约去东涌绿道是去年冬季最冷的一天。那天冻雨簌簌,寒风阵阵,南方特有的湿冷简直不让人出门,让人想一直把自己锁在家里睡觉。可是已经和大家约定好了,于是带着复杂的心情出了门。 坐在开着暖气的车里,听来过的朋友介绍,位于广东省罗非鱼良种植场边的这条绿道建于2011年4月,是一条沿着河流所建的人工廊道,一段长1.5千米、高3.5米的瓜果藤条棚架小路最值得一去,春有芽、夏有花、秋有果,在这条花繁叶茂、瓜果飘香的绿道上,或骑车、或步行、或谈天、或静思,都是花费时间不多却能所货颇丰的益事。 有人问道:“冬天有什么呢?”众人无语且懊恼。而我则无所谓,因为我是奔老丝瓜去的。 下车后,身体的暖意瞬间被寒冷吹散。然而,此刻的绿道让人惊喜,它褪去春的喧嚣、夏的热情、秋的暧昧。棚架上的叶子已落去,走在绿道上,映入眼帘的是蒲瓜、千成兵丹、蜜本南瓜、长柄葫芦、西番莲、刀豆等,两旁塘泥俱现,几根木棍漫无目的地斜插其中,静候来年的忙碌。 时值深冬,瓜果不密,因此远远地就见到悬挂在棚架上瓤成粗网、参差不齐的老丝瓜,密密麻麻,多不胜数,“漂亮的身段”显示出它们在夏季的英姿。枯黄的外壳有的已经裂开,白色的粗网若隐若现,我一下子就看上好几条丝瓜,像个孩子似地蹦蹦跳跳,想要把它摘下来。无奈衣服穿得太厚,碰不着丝瓜。有几次碰着了老丝瓜粗粗的“皮肤”,却还是不能连藤拔下,反倒棚架上的碎雨淋了一头。不觉间,已微微出汗,擦擦汗,像擦去了生活中的压力,也许已经是童年时代的感觉,带不带老丝瓜回去都不重要了。 可一路还是想着丝瓜,想蒸丝瓜的甜,想炒丝瓜的嫩,想着小时候的味道。 那时,家有凉棚,种满丝瓜。每到夏季,凉棚下长长短短的丝瓜欢天喜地地垂下,我会蹦蹦跳跳地伸手去摸它们,它们一天一天往下长,我一天一天往上长。吃饭前,妈妈会在院子那头喊:“摘两条,选大的。”我坏笑着从角落里拿出三四条,有大有小,忙不迭地送到妈妈的手中,一会儿,一盆香香的、嫩嫩的丝瓜便上桌了。 朋友说,夏秋再来,那时候丝瓜正绿,带着极嫩的黄花,可以摘取一些,然后送至绿道附近充满疍家风情的“御鹿苑”,院里有师傅帮你把丝瓜进行处理。要知道炒丝瓜可是大师傅的绝活之一。炒丝瓜也是绝活?正是!把最家常的小菜炒得能唤起童年的味觉与记忆,难呀! 这时候想起小时候最爱的一段绕口令:“正月到姑家,姑家未种瓜;二月到姑家,故家正种瓜;三月到姑家,姑家瓜发芽;四月到姑家,姑家瓜开花;五月到姑家,姑家瓜长瓜;六月到姑家,姑家正吃瓜。”童年时代就是这样,东涌人家亦是这样。夏秋的傍晚,伯父阿姨、姐妹兄弟,一大桌子人坐在丝瓜棚架下,在桌子上,放着炒丝瓜等几样小菜,粗茶淡饭,摇扇唤犬,谈天说地,看夕阳褪去最后一道光亮,看繁星盈挂在空中。 丝瓜是吃不腻的,因为做法太多,如同它的别名一样多,我妄自分了分:有根据它的长度来起名字的,如“天罗”、“天丝瓜”、“天罗瓜”、“天吊瓜”;有根据它的内部结构来起名字的,如“绵瓜”、“絮瓜”、“天络瓜”;也有根据它的用途来起起名字,如“布瓜”、“洗锅罗瓜”(老丝瓜干枯后可以用于洗碗,干净而清爽);它还有个谐音外号叫“喜瓜”。 夏秋来时,我们再来一品丝瓜吧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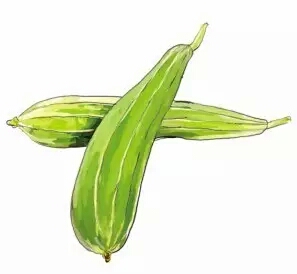

我常常想起东涌绿道上那粗大的丝瓜。果实成熟后,如果不摘,再过几个月,绿丝瓜会变成老丝瓜,透着如同发黄的旧报纸般的颜色。彼时,瓜囊已经干枯,成了丝丝密密的网,再摘下,便可做成洗碗的布;又可煮成下火的茶(丝瓜络味甘、性平,据说可以通行十二经,故名“络”,取“通络活络”之意,是清热化痰的良方);再或者结绳挂在厨房一角,成为一件古朴的装饰品。
(排版、校对:琪琪)
